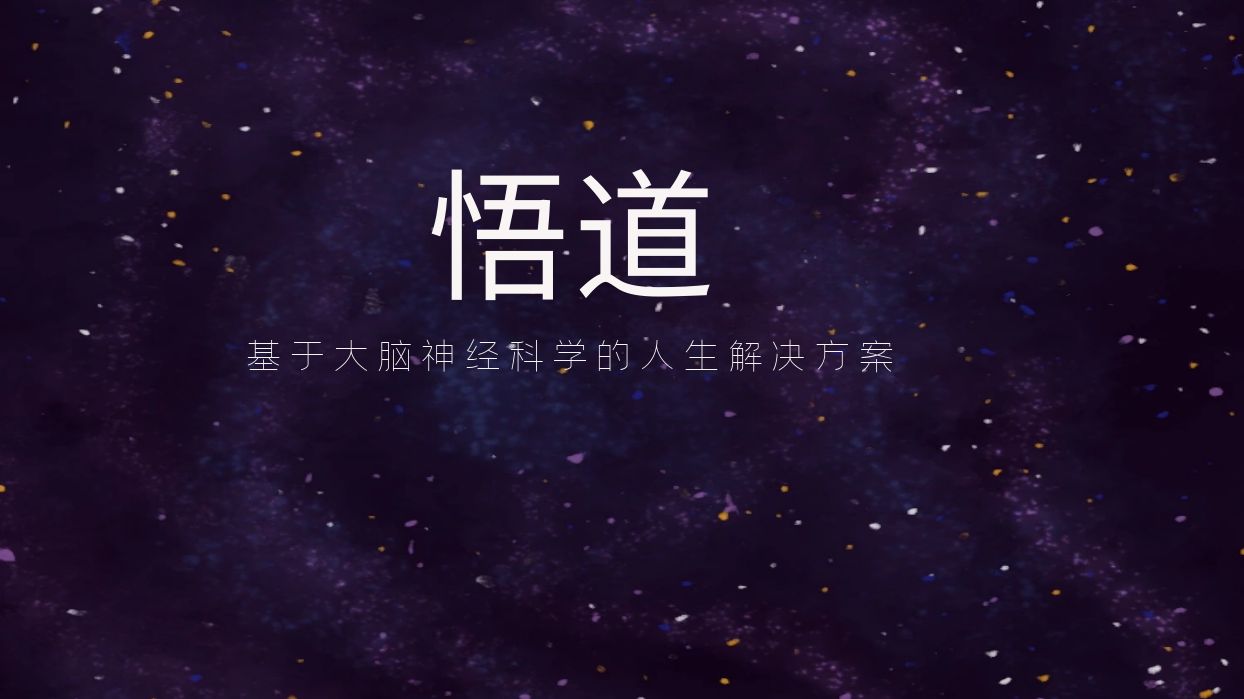网球【第二阶段】
网球【第二阶段】7000
0425周一【第九次单打】
阳光日,刚打完网球回来。
刚过去的2周,似乎一直在下雨,我此前提前4天订了今天的场,大概看着天气预报订的,没想到今天果然可以打,这是莫大的恩惠,这种恩惠还被另外一件事情衬托着,那就是在刚过去的一周,我生病了,可能是急性食物中毒,先是肚子极度的痛,半个小时,甚至痛不欲生,然后拉肚子,全身时不时发痒,这是第一天的症状,在接下来的4天,肚子痛的程度随时间下降,但是发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在这期间,只要吃东西,胸口就堵,感觉肠胃不消失食物,于是开始控制饮食。
我现在生病有个信念,就是要依靠我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恢复,不吃药,到了第四天,其他症状开始缓解,但是痒的程度加重,妻子一直建议我吃药。
实在没办法吃了一颗搞过敏药,和整肠丸,随后2天,我都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这颗搞过敏药的威力,我有点混混沉沉的,头脑相当不清醒,感觉相当疲劳,整个人就是想睡觉,平时晚上我一般都要23点后才睡,那几天大概都在21点。
在这些病痛的对比下,今天是生病后的第6天,我基本已经恢复如往常,加上还能去打这场网球,这实在是人生一大恩惠。
今天是第9次单打,我又有新的收获或突破了,此前的几次有点卡住的感觉,但是今天做到了此前无法做到的状态。
发球时
以往发球时,我眼前会先于声音看到球落地,我在此前描述合一状态是只看球,但是我往往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似乎有看又似乎没看,因为这个过程是毫秒级别的,它极容易漂移,有时候觉得有,有时候觉得没。
我发现,倾向于“没”的时候,实际上,我的眼睛的注意力跑到球的落点上了,于是,我今天加了一个要求,不看球的落点,只看我发球的时候,击球的瞬间的“球”,如果我看得足够清晰,足够细致与足够“久”,我几乎是先听到球落地的声音,然后才看到球,此时它意味着,我的注意力都在击球的瞬间上,而不是去关注球到底有没有在界内。
这是一个更“无我”的状态。
它意味着,球在界在与否,我都不关心,我只关注我击球的瞬间,反过来,我们经常之所以关注球是否在界内,是因为我们“怕输”,想要球在界内。
外界“多线程”的干扰【越多干扰度越大】
于是,我每个动作每个动作尝试达成这个状态,我发现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程度的击球状态,比如最可控的是发球,其次是拉发球,接着才是正拍或反拍,那么这种所谓的“最可控”,是干扰度的体现。
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接发球,对应的是我们在同一时间,外界到底有多少“线程”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发球时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线程最少,因为它不需要移动,更不需要关注“对方”。
特别是“对方”这个因素,假如我们特别注意对方,当他上网时,我们知道他上网,此时我们的击球就会因为对方“上网”的这个行为而有所调整。
而发球时,我追求完全不关注对方,不管他如何站位,都不会影响我如何发球,我甚至都不看对方,我看一下他,是为了确认一下他是否准备接球了,至于他站在哪里,我完全不关注,我的所有注意力,都在发球上。
干扰度其次的是接球,不管对方发什么球,不管快还是慢,我只管看准球就打,每一击都是全力以赴。
正手与反手
我的反拍是双手拿球的,我发现我的反拍可以更容易地做到与发球时一样的状态,即我几乎也是打完球,眼睛还是停留在击球的瞬间,听到球落地的声音后,我的视线才看过去,我的所有的聚集点都在自我的击球上,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对方如何跑位,在哪里,完全不影响我击球前的瞬间,我没有任何犹豫感。
我甚至在听到球落地声音前,我都完全不看对方。
与我的正手相比,我发现竟然是因为双手反正,它的打法更多的是“关闭式”的击球,这种关闭式迫使我无法及时看对方。
而我的正手是开放式的,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面对对方来击球的,这使得正手在挑战这种合一击球的难度提升。
而这里的区别,竟然跟站位与眼睛的视角有关!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只要我们眼睛看不到,我们就不会产生情绪!
于是,在随着的尝试中,我试图把正手也调整到“半关闭式”的,此时,我的视角变窄,我得到更好地专注在击球上。
上网
干扰度或者说影响度最大的是上网,当我上到网前时,我的注意力往往会在对方上,它的意思就是要“看对方的位置来决定把球击到哪个位置”,但是此时产生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我的眼睛都跑到对方身上时,我就看不到球【显意识】,此时的击球行为与动作,完全是靠潜意识的自动化本能。
我每每在犯这样的错误后,我就告诫自己要看球,而不是关注对方,但是只要我一上网,我又会不自觉地关注对方。
此时,另一个原因在于,只要上到网上,我们眼睛看到对方的概率变大了,几乎就一定会看到对方,而对方的任何一点动作,都会自动化的劫持我们的主动显意识的注意力。
当这个主意识被劫持的时候,网前截击就只能靠潜意识的线程了。
因此,我上网失败率极高。
我的对手是上网型与全面型的,他几乎就是我的克星,他会有很多上网,很多放小球,一旦他放小球,就意味着我必须上网,当我状态好时,我上网的回击质量会非常高。
当他上网时,我的注意力也非常容易被他干扰,此时,在观察到他的移位与站位后,我就会调整击球方式,这是非合一状态,我在这样的状态下,失败率极高。
在经过多次的调整与自我告诫后,我也开始可以很多地执行我前文描述的状态,即我的眼睛完全只要我自己的球上,在我击完球前,我完全都不知道对方已经上网,此刻,我只知道我自己,我全力以赴的打那一球,不会因为对方的上网而调整击球方式。
这是我击球时的最高境界,即使对方已经上网,我甚至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只要我们眼睛没看到,我们就不会产生情绪,只要你能够完全忽略对方的存在,你就不会因为对方而产生任何情绪。
眼睛看不到是忘记输赢,水掉想要赢的念头
0425双打订场后
938
刚刚9点半订到了周五早上的网球,于是就在想着,要约单打还是双打,昨天周一刚打了一场很过瘾的单打,双打完全是另一波人,大家更多的是娱乐,锻炼与聊天,最终我还是决定约双打,一方面,我并不想”绑死“在单打上,不想过度执着这个东西,它太好了,但是我一周有一次就够了,另一次,就是要用来娱乐的,甚至我到场上走走也开心。
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对抗赛单打中,我能够实现合一状态,那么在更多交际的双打中,我也想尝试保持更多合一状态,双打是难的,因为人太多了,而且我还有执念,那就是我认为我是打得最好的【事实,至少球齡15年以上】,因此,我有股不自觉的表现欲【这是争与炫耀的本质】。
这样的人生观在于,任何经历都是有价值的,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不仅仅追求在创作,在事业里面保持高程度的”合一“状态,当我在家务里面或者陪家人时,我同样在追求”纯粹度“。
某种程度上来说,双打是4个人甚至6个人,即使下场休息,也有2个人,此种状态最难觉察。
家也一样,当妻子橙子在家的时候,想要保持”有觉知“的纯粹做事,陪家人状态,那么难度比我在坐在电脑前难,而且难上无数级别。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个人与公司,当我们处于团队里面时,往往不是我们引领团队,而是团队观在不自觉地影响我们,决定我们,扰乱我们原本清晰的思路,点燃我们的情绪。
环境中的任何时候的”另一个人“的存在,都是”“要命的,因为他随时会点燃我们的本能自动化,引爆我们的本性,而我们完全不知道,还以为是自己选择如此做。
0429双打
0657记录
36分出发,50分到,发现还没有人,于是在找球中,果然找到3个,到底我是贪婪还是,还是能够走路,我并没有任何情绪【比如抱怨球友们迟到】,反正就是走路。
7点L爸和Y爸到;
0813他们4人到齐了,在双打中
1020坐到电脑前记录
930打完回来,回到家,洗了个澡,再吃了点东西,烧水,然后上到三楼,每次这个时候,我都想第一时间记录感受。
今天双打的时候,其他几人都是接触网球没多久的,但是打得都不错,毕竟都是热爱运动的人,羽毛球乒乓球打得都不错,因此发现他们上手很快,只是球感与跑位相对较缺乏。
我试图在跟他们打的时候,运用我在单打比赛时的技巧,但是我发现这完全行不通,单打的时候,我不用照顾对方的“实际情况”,但是我现在面对的是一群新手,我似乎不得不照顾,否则我就是疯了。
这是人之常情的东西,我一个十几年的老手,不可能去跟一个刚接触网球没多久的人较真。
我经常陪橙子打,因此我知道一个合格的教练应该是怎样的,我会尽力地打出不深不浅不左不右,不慢不快,最好就在你正手位的球,这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极度根据对方来打,我的球原本会比较偏向上旋,跟新手打,我似乎得压制自己的这个能力,我得试图打出更多的平击,以便让对方更好的回过来。
对新手来说,他不需要打得多么精彩,他需要的是打出信心;
说实话,他们确实打得很不错,很快,就开始打双打比赛了,我也和一位球友组了一局,但是我们竟然输掉了比赛。
他们把我称作教练,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我跟橙子打的时候,我是他父亲与教练;
当我跟这几位家长打的时候,我可以充当一下教练,但这不是我期待的,我期待的是“朋友间的友谊”,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跟他们一起打,一方面这是我挑战自己的一种方式,即对我现在的价值观来说,即使是走路,我也很愿意,能运动到身体又能建立家长之间的友谊,何乐不为。
当我认为对方是“亲手”时,不管我如何想要认真的打,我就是做不到像单打的时候那么专注,此时,击球质量也直线下降。
这就是我内心事先预设的“念头”,此时,我在打球,但是实际上我的心时刻不在球上,而是在对方上,单打的时候,我的对方不存在,但是现在跟一群新手打的时候,我却只能看到对方,从而反而忽烈了球。
我发现一个问题,当我被放在一个不太一样的位置时,我的心态变得不太一样,我似乎总有一股想要露一手的冲动,比如发球的时候,我会时不时使尽全力地打,结果反而表现很糟糕,因为合一地击打一个球跟为了表现的打,这完全是两回事。
我跟橙子打时,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想要在橙子面前炫耀的情感,也没必要。我从理性上会清晰地告诉自己,即使在这群家长面前,我也完全没必须,但是这种告诫似乎没用,人的炫耀感完全是内置到本性的自动化层面的。
在任何运动上,我发现我都有这股情绪的存在,因为我向来对自我的运动细胞相当自信,我在每一样运动上,都会觉得自己是“有一些运动细胞的”,是更厉害的。
这种“比”的情感深深地根植在我的本性中,时不时地困扰我。
它来的速度非常快,时常发生了后,我还不一定能够第一时间意识到,甚至更多的时候,往往要等到像现在这样的事后觉察,才能感知到它到底在如何扰乱着我。
因此,另一方面,正如我在这场双打前预感到的,当人多的时候,我必定是用本性在对接着一切的,因此,我想借这样的机会,来辅助我更清晰地看懂自己。
对于感知来说,当一个环境中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除了会调动本能自动化应对着的同时,我们也是接近无感知的,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我想挑战一下在那种情况下,保持较高的觉察与感知,但是依据今天的情况看来,我几乎都是无感知的。
1444【喝茶时手机创作】
刚刚下去把汤和饭分别定时上,通菜也先摘好泡洗着,这样就可以一直到四点半才下去,炒个菜就行了,真方便,一大恩惠,也得益于刚刚遛完狗了。
今天是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也想着一会喝茶后再去写写文章。
其次,昨晚紧急核酸检测后,发现我有一股想要去查看新闻的冲动,但是我没有,我还是不想让太多无关紧要的事情占据我难得的思维,对于思维来说,少和慢就是它的通道,
正如我此刻,就是坐着喝茶,手机只在记录,不刷朋友圈也不闲逛。
早上打网球的家长都打高尔夫,他们一直在我面前聊,我只是默默听着,一方面我的运动项目足够多了,另一方面我在家也有快感,事业也有快感,足矣,多一个项目,第一份分神,人生最珍贵的是悠闲可以自由琢磨的主动意识。
之前家长聚会,大家聊到旅游,有一位说自驾游去过西藏多次,我能感觉到他神情中的自豪感,甚至有人说要开房车上路。我同样只是默默听,老子说出门跑得越远越无知,我以前事业生活都找不到价值的地方,也常常向往这种旅游生活。
我现在也完全没有这种向往了,我一点都不想逃离眼前的生活,我甚至每天醒来都是充满激情与渴望的。
打球的时候,有家长说放假了有时间去打高尔夫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我要逃离家庭自己去享受去。
当我在计划自己的项目时,我一定是错开假期,我只选择在工作日打球,假期是要陪家人的,家也让我充满乐趣。
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们一直在我面前聊高尔夫时,我没有想要的冲动的一大原因。
比如,同样是陪孩子到村里广场运动,有些家长就把这个过程定义为“陪”,是付出,我正好相反,不管陪橙子完什么项目,我都试图从这些项目里面找到乐趣,此时我是在得到,而不是在付出。
比如遛狗,我经常看到有人骑电动车遛狗,我跟知了出去的时候,我时常对朋友开玩笑说:“让知了遛一下我们”。
我经常这样想,有了知了,我走更多路了,我还每天给它梳毛,各种在它身上的忙,如果没有它,我大多数时间一定是坐着,现在我各种走各种忙,反而不自觉锻炼了身体,与我长期坐着创作的职业形成一个平衡调节关系。
因此我时常反问:“到底是我在恩惠知了,还是知了在恩惠我”;
我还会把这样的反问进行排比式的罗列:
- “当我在陪家人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到底是我在恩惠家人,还是家人在恩惠我”;
- “当我在全力以赴琢磨创作的时候,到底是我在恩惠用户,还是用户在恩惠我,而我还得到了收益与认知网络”;
这样的认知让我越来越具有在做这些事情时的情感与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逃离感,反倒是更期待在家务里面,陪家人,照顾知了和沉浸在事业里。
当我在家,家务,家人和事业里面全面得到价值观的时候,我越来越具备一个能力,即我越来越应该纯粹地做着每一件事情,而且往往能够带着感恩之心的力量感认真的心甘情愿地想要做到最近的做事。
我越来越坚信每一件事情都是天道,当我对接到天道的时候,我就能够享受般地做着那件事,此时我是有觉察的,接近于觉醒状态,在“动物脑的自动化之外”的状态,此时大脑分泌真实激素,使得我可以专注,认真,享受,此时前额叶的主动意识在线的比例相当高,此时它往往表达出如下一些外在的特征:
我是极慢的,排它式的【显意识是单线程的】,因此我往往会忽略眼前的一些事情或人,妻子批评我对橙子说:“你爸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他也表达为我对眼前的事件的当机或中断状态,必须抽离出来
16点02【电脑前创作】
得益于下午2点的时候我已经把晚饭的一些事情定时好了,于是我现在可以坐到电脑前,继续创作。
前面的这一段,是我刚才在四楼天台坐着喝茶时,用手机记录的,这个状态往往是感知的时候最纯粹的,我因此感知到了非常多对比素材。
当我提到做事业的“纯粹度”时,它往往意味着我们思维的宁静度与琢磨事情的深度,“深度”这个词很重要,我们经常会说:“深度思考”,用大脑的话来说,就是整顿到的“信息量”,我把觉察或整顿描述为:“用知识点整顿真实经历”,它就像图书馆管理员用一个编码来编码图书一样。
我曾经用“整理家里的物品”作过说明,比如我一楼有一个杂物房,里面有一个工具架子,架子的第一层摆放一种类型的东西,第一层是“狗的物品”,第二层是橙子的玩具,第三层工具大集合,比如扳手,螺丝刀这类东西,第四层是我的运动用品如网球拍,网球等运动器材。
这是这个架子的“规则”,这就是规律,也可以描述为“知识点”,任何时候,当我要去找一个物品的时候,我只需要按着这个规律【知识点】去寻找,我就可以找到想要的东西。
杂物房还有很多东西,大体都按照一定的规律摆放的,因此知识或者规律,就是为了“预测”,为了更高的效率。
如果这些东西全部不进行归类,零散地存放在杂物房里面,那么每次我去拿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可能要找半天,此时,它就表达为,我们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慌乱没有对策的现象,我们完全找不到相应的“知识点”来应对事件。
那么,这里涉及到两个点:
- 一个就是经历,不断增加的经历【正如不断增加的家用物品】;
- 第二个:觉察,整顿,整理与编码【归类】;
正常情况下,我们最可能的状态就是活在第一种里面,也就是我们不断经历,但是从来不进行有效的整理整顿与编码,或者说,即使我们想要进行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么重要。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我们一直在追求知识,在逻辑上学习大量的知识,这正是我们今天学校教育的特征,我们实际上都有“知识匮乏恐慌症”,我们生怕落后,于是我们拼命读书,拼命看书,这是我几年前的状态,我形容“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记忆知识,试图一口气把所有的知识都装进脑袋,我在这个状态上,焦虑地持续几年,这种无效学习的现象,最终把我推向了探索背后天道之路。
我现在告诉你道理,让你知道要“进行整顿与编码”,但是这个道理无效,你最可能的状态就是做不到有效编码。
这首先来自于我们每个人在今天都面临着一股“不得已的被动驱动力”,它呈现为“焦虑感”普遍地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结果就是,即使我们想要“整理一下家里”,但是我们却是仓促的,想要赶快整理完的。
着急着,焦虑感与压力感正是编码的第一大敌人。
《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模型》解剖的第一股力量,正是这个东西,这是人性里面最为根本的力量,我们都活在它里面,在它里面相对性的做着事情,除非我们能够跳出它来,“在它外面”活着。
它就正如我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当我在这里记录或创作的时候,我实际上也在跟它对抗着,我时刻在跟它对抗着,它就表达为我不断提到的“我一直在追求做事业时的纯粹度”。
这就是“有效编码”的难度;
当我们处在这个恐惧力量的笼罩中时,我们的思维一定就是肤浅的,此时编码的效果就会很差,很难具备知识可以有效指导生活的能力。
当我在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只能是感慨,因为每个人都具备天才的头脑,但是却被一股“力量束缚”着,这股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能够跳出来摆脱它遮蔽的,少之又少,因此我只能感慨。
这条路太长了,有时候用一生都走不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来构建一些,必须非常坚定地做这样的事情,
5月3号【第十次单打】
早上545就起床了,6点14分出发,629到球场,球友40分到,打到830,去学校接橙子回家,准备野餐的食物。
这一次,到了球场后,球友说他的背因为上次发球,受伤了,发不了球了,说我想发可以发。
于是我不断发,他问:“一直发会不会枯燥?”,我:“不会,我一直在挑战自己”;
我一直在找,如何每一拍的发球接近合一的状态,那么它的意思就是,此时不管我有没有在打比赛,我单独发球的那一瞬间,就是一个独立事件,在这个独立事件里面,我追求全神贯注,全力一击。
当我们打比赛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容易以比赛为导向,而在我的追求中,即使我在比赛,那么“比赛也不存在”,也就是事实上我身处在比赛中,但是它完全对我没有影响,仿佛不存在。
于是,当我们真的没在打比赛的时候,那么我的状态依旧一致,不会说没有了比赛,我就没有了打球的激情,有所懈怠等,而是恰恰相反,如果我能保持合一,那么我的激情不会被有或者没有比赛影响。
因此,当我在比赛中或者没有比赛中时【在下棋中或者没在下棋中时】,我均保持同样的状态。
发累了,我们就底线拉球,我越拉越勇,越拉越有气势,我完全沉浸在研究如何让回球变得更有质量,精神集中,一点也没觉得疲劳。
结果,我们竟然拉球接近2小时,当我提前半小时撤退去接橙子时,球友还依依不舍,说还想再打。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更多精彩内容